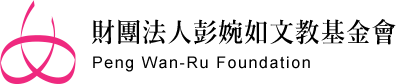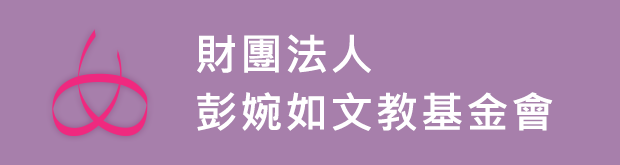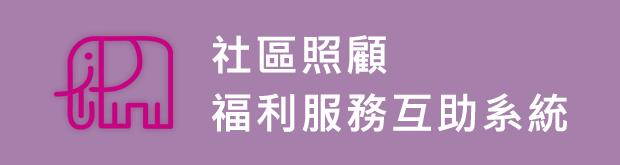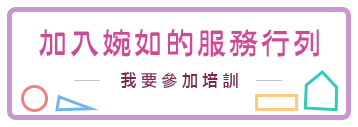您在這裡
【小大公民生活誌vol.1】孩子的人權探險,從友善職場開始!

攤開幼兒園的行事曆,會發現每年 11 到12 月,園區會舉辦一系列的「兒童人權活動」。這是為了實踐聯合國於 1989 年 11月 20 日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更是配合「國際兒童人權日」,在這段時間藉由與家長及孩子共同舉辦活動,讓所有社區中的大小朋友有機會認識兒童人權的價值。
不過,「權利」這麼抽象的概念,對許多大人來說,都還是很新的思維,畢竟這世代的父母從小成長和受教的環境多半都是「囝仔人有耳無喙」,甚至是打罵教育的記憶;而專業教保人員養成的過程,或是過去的工作經驗也甚少談論人權的概念,更遑論實作的經驗。因此,當老師們聽聞要規劃兒童人權課程時,迷惘與不確定是真實的反應。
臺北市臺北捷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A老師坦言:「剛開始還沒有想法,雖然知道兒童人權的幾個項目,但沒有太多深入思考要怎麼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的D老師則是直白的說:「很疑惑,沒有接觸過」。
如何建立老師們對平等尊重和參與爭取的先備經驗?
這就需要透過創造具體的情境和目標,讓老師們能在日常生活中深刻體會到自己的權利及尊重他人權利的重要性,而能成為孩子身教的榜樣。
看見孩子前,先讓老師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現任北區督導,也是前任臺北市臺北捷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主任的蕙琪說:「我回想自己在從事幼教工作時最開心的時光,便是能安心從容地與孩子好好互動。於是我也想努力創造這樣的工作場域,讓夥伴在成為幼教老師的同時,也能好好地被對待。而營造平等、尊重、友善的工作環境便是第一步。」
她提及過去在私立幼教產業的工作環境與經驗,在那裡,老師往往被當成工具人,在開會中只能被動的接受主管佈達的指令,然後執行。個人的工作表現往往以成果來評斷和檢討,但過程中的付出和努力卻很少被看見。
蕙琪以一位新進C老師的例子說明了不同對待方式所帶來的轉變。
蕙琪説:「不知道是還在適應,或是個人特質的影響,只要這位老師在班級氣氛就比較緊繃。孩子會比較靜,夥伴們也不熱絡。我觀察之後,在晤談時先謝謝她願意接下幼兒園老師這份工作的挑戰,並表示我有看見她對自我的要求,與相應而來的工作的努力。老師紅了眼眶回應我說:『過去大家都說我帶的孩子很辛苦、壓力很大,但謝謝妳有看見我只是想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後來透過持續的溝通,才慢慢讓老師卸下被檢視,進而轉嫁到自身和他人的壓力,和孩子跟其他同事互動也愈來愈放得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教保中心的E老師則分享來到這裡的經驗說:「主管不是佈達事情,而是互相討論商量,有些事情像是法規不能調整,但是有些是有彈性的。例如有一個疑似特生的孩子,老師不確定要怎麼拿捏跟家長溝通的尺度,所以開會的時候提出來。一開始大家想不出來,後來有一個老師說不然把家長找來當志工建立關係,主管就說:『好啊!為什麼不行?』那個感受是我講的話大家都有在聽,意見有被採納,感覺就會很好。以往的經驗是主管會直接把我推出去自己看著辦。」
B老師也分享了她的感受:「沒有想過原來學校的事情是由大家一起決定的。在這裡大家是可以互相溝通的,不會因為彼此的經歷、年紀,或是職位的不同,而把一些話藏在心裡。當我們發現問題的時候,大家是可以提出來一起思考策略,然後想辦法解決。」
就像開放教育所強調的「看見孩子」一樣,要求老師面對孩子的態度,是能站在孩子的旁邊,而不是對立面。因而,陪伴孩子成長,關鍵在於如何觀察孩子的實際表現。我們需要理解孩子在過程中做到了什麼,發展了哪些能力?經驗了什麼挑戰,以及有哪些需求和困難需要克服。這些觀察不是為了檢視孩子有沒有達到既定標準,更是在過程中保持耐心和開放的態度,和孩子共同發現並體驗成長的點滴,同時適時地引導和建議。
這樣的態度和過程,其實跟引導老師以及帶領工作團隊,共同搭建出平等尊重的互動環境是一樣的。
如同蕙琪所言:「引導老師的過程,當然仍是在一定程度的風險管控下進行。透過個別晤談或是團體會議的方式,但關鍵是拋出議題,讓老師去思考和討論,主管提供的是建議,老師跟孩子互動的時候也會是提供建議。當最後的決定是老師跟孩子自己下的,更能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平等尊重,讓學習自主,充滿關愛
這種被聽見和得到尊重的經驗,也影響老師日常面對孩子的態度並能發展兒童人權課程。北捷教保中心的A老師說:「就像主任會聽取我們的想法之後,再去調整我們要做的事情。那當然我們在做兒童課程的時候也一定要去聽一下孩子的聲音,他的意見、他的想法是甚麼,之後再一起討論出最好的方法,一起執行。」
蕙琪分享了他觀察幸運草村孩子打果汁的實際情境,老師引導孩子們討論如何製作香蕉牛奶,當進入果汁機的步驟時,孩子們藉由討論評估花 21 秒應該就能完成果汁製作。老師也鼓勵他們嘗試,試過之後,師生一起發現時間真的太短了,沒有攪拌均勻的效果。於是孩子們在這樣的實際經驗下,決定拉長果汁機打果汁的時間。
蕙琪也看見老師在理解「處罰」這件事上有新的想法。很多老師會有一種「直覺」:當孩子做得不夠好,就安排讓他一直練習,他就能做得更好。老師自認這麼做是立基在「為你好」而非懲罰。比方「玩具收不好」的同學,就一直被指派任務當小幫手。有天,孩子透過家長向園區表達他在這過程中感受不好。面對這樣的情境,蕙琪也在會議上跟老師們討論,蕙琪向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問問老師們的感受:「如果你會議記錄寫不好,那我就安排之後每一次的會議記錄由你來做,讓你多多練習,你會覺得這是為你好?還是覺得是懲罰?」全部老師就笑出來了。
老師回到班級,轉而在團體討論的時間,帶孩子一起討論班級中「愛丟玩具」或「不收拾玩具」的問題,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一起解決?過程中就有孩子舉手發言:「那我們是不是要提醒他?」。透過開放孩子參與討論的過程,不僅讓孩子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也帶起孩子對班級運作規則的共識,讓學習更有歡笑與合作的氛圍。
中區國稅局教保中心的F老師也說:「以前的園所是一切都要靠自己,搭檔比較被動,向主管反應也得不到協助,就是感覺求助無門。但在這裡像是昨天,當我情緒上來的時候,其他村的老師觀察到就來把孩子帶走,神救援我。我感受到她們幫我,就說:『不好意思,我情緒上來了講話比較大聲』,她們就說:『沒關係,互相幫忙啊』。(這樣的經驗)就真的會影響到面對孩子的態度。以前孩子哭我就是讓他哭,但在這裡後來我就會跟孩子說:『那你哭完覺得好一點再來找我,我等你,我在這裡,我會幫你』。主管和環境怎麼對待妳,妳就會用這個方式對待孩子。」
E老師也笑著說:「我們彼此幫忙的時候小孩都在看,就會發現最近有大班的孩子也會去關心其他的孩子,問他說:『你還好嗎?』或是跑來找我們說:『老師他想馬麻了~』」
我們發現,當老師的「尊重個人尊嚴的權利」、「參與權利」及「表達意見與被傾聽的權利」得到確保,就更有機會用同樣的方式面對和引導孩子,真正體現兒童人權的價值。這不僅僅是搭配11月的兒童人權活動,更是實質融入日常生活的人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