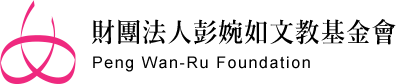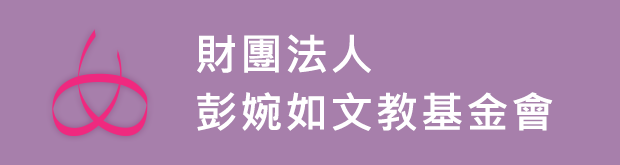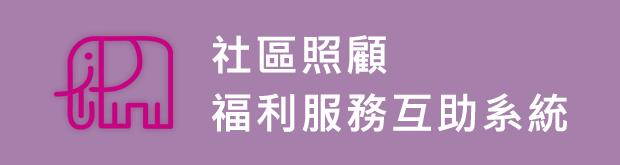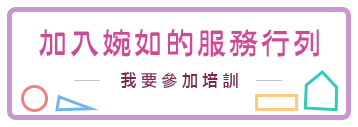您在這裡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
本書於1995年出版,共8位作者,分別就社會福利、法律、參政、工作、教育、健康與生育、性暴力等方面,呈現並分析台灣婦女的處境,進而提出政策建議。此處附上書中「前言:女性學學會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與「結論:男女共治共享的國家藍圖」2篇章。
目錄
- 前言 女性學學會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劉毓秀
- 社會福利篇 建構女人的福利國 傅立葉
- 法律篇 男人的法律,男人的「國」「家」:「民法親屬編」的意識形態分析 劉毓秀
- 參政篇 台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興體制外的觀察 梁雙蓮、顧燕翎
- 工作篇 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 張晉芬
- 教育篇 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 謝小苓
- 健康與生育篇 國家政策之下的女性身體 劉仲冬
- 性暴力篇 解構迷思,奪回暗夜:性暴力之現況與防治 羅燦煐
- 結論 男女共治共享的國家藍圖 女性學學會
-------------------------------------------------------------------------------------------------------------------
此處附上書中「前言:女性學學會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與「結論:男女共治共享的國家藍圖」2篇章。
篇名:前言 女性學學會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作者:劉毓秀
1993年9月28日教師節這一天,女性學學會宣布成立。六十幾位創始會員中,絕大多數為大學女教師,少數為女性文化工作者。這樣的組合所構成的婦運行動團體,標示著台灣婦運的一個里程碑:觀點、知識、行為模式深受全球性第二波婦運影響的年輕一代女性,有相當數量已進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領域,而且,她們顯然決定要兼跨學院內外,融合學術與行動。這並不是說在此之前的台灣婦運團體或路線已經過時,相反地,這意味著台灣婦運得到了一支生力軍,它要跟其他婦運團體連線奮戰,加速男女平等的一天的到來。
在以行動團體的姿勢度過忙碌、緊湊的第一個年頭之後,我們得到深切的感受:一方面台灣兩性關係轉型的時機已漸趨成熟,它即將牽動廣泛的文化和制度變革,可是另一方面,長期的資源匱乏使台灣婦運有著強烈機動性的特質,以致一直缺乏對台灣婦女處境較為精確的全面性掌握,而且,也欠缺明確的宏觀方向。我們開始思考:在這個關鍵時刻,女學會做為一個兼跨學院內外的團體,能夠為台灣婦運和台灣社會提供什麼特殊的貢獻呢?
無疑地,女學會成員所能提供的,便是我們作研究、從事思考的專業訓練。我們於是擬訂第二年的工作目標,結合不同專長的會員,展開《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的撰寫。此舉目的乃在於嘗試描繪台灣婦女現況的全貌梗概,並且,試圖從一個較大、較遠的角度,勾勒台灣兩性平等的未來。我們希望,這樣能夠幫助台灣婦運更有信心地向前邁開腳步。
這本《白皮書》撰寫的過程和方式有必要在此加以交代,因為它無疑關係著本書的基本精神。本書的寫作者共有八位,分別負責就福利、法律、參政、工作、教育、生育與健康、性暴力等方面,呈現及分析台灣婦女的處境,並提出政策建議。這八位撰寫者,加上女學會理、監事(兩者有一部分重疊)總共十三人,組成《白皮書》工作小組,參與《白皮書》醞釀、寫作和定稿的整個過程(這十三人除了八位撰寫者之外,還包括張小虹、瞿宛文、林芳玫、鄔佩麗、胡錦媛)。需要這麼多人長時間共同參與,主要原因有二:(一)女性處境和婦運議題面向甚多,錯綜複雜,需要不同學域的專家共同會診。(二)婦女問題癥結極深,若要認眞解決,而不是敷衍應付,勢必牽動社會和文化架構的重大轉變,這重大的轉變若要成功,必須靠整體社會達成共識,動力追求實質的公平和諧。《白皮書》的集體參與,代表的便是尋求共識與全面掌握婦女議題的努力。
本書所採用的方法,是將現有的制度、政策、法條、社會狀況、統計、研究、調查報告等等,拿來作比對、分析及詮釋,試圖拼出婦女處境的各個面向。在這樣做之時,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雙重觀點——
一方面,我們秉持婦運的觀點,著眼於揭發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並尋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我們也以社會所有各方(即一切人我、物我關係的各方的永續平等共存為基本考量。也就是說,我們追求性別、階層、族群、長幼、人與自然環境......的各方的永續平等共存。
以上的雙重觀點所期待的國家和社會架構,以及制度與政策,應根基於對「永續等共存」的真誠信念,致力於針對不平等、有害共存的現況,隨時進行有效的調整和解決。如此,將權力和利益集中於特定權貴的父權資本主義制度,可望平順地融解於全民民主體制中。這追求全民富足、平等的體制,相信在台灣是有肥沃的土壤的,只等著我們去耕耘,因為台灣人民已經不斷地以自發性的行動證明,我們最看不慣的、最不願意忍受的,就是「不均」。解嚴前後所蓄積的打倒專制與特權、追求公平分配的強大動能,若能導向追求社會所有各方——包括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共存,相信建立美麗新台灣的夢,實現的一天並不遙遠。
鍥而不捨、蓬勃不衰的台灣婦運,包括這本《白皮書》的出版,顯示台灣女人勇於爭取對社會現狀的詮釋權,和對未來走向的發言權;我們女性所爭的,不僅是權力,更是責任——這是從女性本身的觀點自發地貢獻社會的責任。我們很清楚,台灣婦運毋須背負「捨我其誰」的悲壯重擔,因爲蓬勃的婦運只是台灣蓬勃的社會運動——也就是既爭權也爭責的運動——的一環。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有足夠的韌性,台灣社會的成功轉型應是指日可待的。
女學會於去年九月宣布《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的撰寫之後,國民黨婦工會不久也宣布她們要進行《台灣婦女政策白皮書》的編撰。本《白皮書》跟國民黨婦工會版本的最大不同,除了前面所提過的集體參與、共識凝聚之過程以外,還在於完全自費、自力、獨立從事研究和撰寫,因此具有較強的批判性。本《白皮書》會經申請國家學術主管機構國科會的資助,但顯然由於本研究不符合主流學術所認可的「社會科學研究」或「婦女研究」的框架,因而未獲補助。除此之外,由於本《白皮書》的參與成員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因而不會尋求或接受任何政黨或政府、民間機構的資助。
獨立自主,尤其是知識和觀點的獨立自主——這不正是婦運的夢想嗎?這無疑是足以令任何女人雀躍興奮的事!因此,本《白皮書》撰寫過程中的眾多討論會,莫不是在興奮、歡躍的氣氛中,聚精會神地進行的。尤其是,在這個過程中,女學會同時進行著各種有關婦運議題的演講和公聽會,包括「1995年婦女節女學講座」、「廢除國家特考的性別歧視公聽會」、「從警政、社工與醫政落實性暴力防治公聽會」、「落實校園性暴力防治公聽會」和「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公聽會」等等。除此之外,其他婦運團體也頻頻有所行動,展現空前的活動力。這些婦運的實際行動,跟本《白皮書》的撰寫同步進行,顯示的是:我們除了追求忠於女性觀點之外,也積極尋求女性觀點的實踐。本《白皮書》所展現的,因而是一種坦誠面對自我處境,並積極尋求自我實踐的女性觀點。
本《白皮書》是女性類似嘗試的第一次,我們深知做得並不周延。有關台灣婦女的一些面向,譬如婚姻暴力及其防治、原住民婦女現況等等,本《白皮書》並未能涵蓋;所呈現的八個面向,資料的搜集有所疏漏,所做的分析也不盡周密;此外,本《白皮書》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與所描繪的男女平等藍圖,也可能失之於粗糙。所有這些缺點,我們都知道難以避免。但是,我們確信,台灣自發性的婦運有了這第一本《白皮書》,便等於有了描畫婦運全貌的第一幅底稿,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有效地進行自省和前瞻。而往後各方的意見,則將成為我們撰寫下一部《白皮書》時的重要參考。
劉毓秀
1995年7月於台北
------------------------------------------------------------------------------------------------------------------------------------
篇名:結論 男女共治共享的國家藍圖
作者:女性學學會
一、女性權益受侵奪的全面現況
綜合各篇論文的描述,我們發現,今天台灣女性權益受侵犯與剝奪的情況,其嚴重性和受漠視的程度,令人驚訝,甚至駭異。底下擬分項加以簡要的描述。
1.<民法親屬編>對女人肆行禁錮與剝削
雖然我國《憲法》明文規定男女平等,但現行<民法親屬編〉卻厲行「男主女從」、「男主外女主內」的制度。<民法親屬編>對女性權益的侵奪,主要係來自於三組法條:(一)跟「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相關的法條,違反《憲法》第十條「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的規定,使女性沒有自主的一席立足之地,令她們淪為夫家的從屬者、服務者,對女性人生產生至鉅的負面影響。(二)跟「夫妻聯合財產由夫管理」相關的法條,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的規定,使已婚婦女沒有自主的財產權。(三)跟「子女從父姓」相關的法條,片面規定妻之貞操義務,執行「子傳父姓」、「父主母從」的父權宗法,使已婚婦女成為夫家傳宗接代的工具,普遍承受著「生子」的巨大壓力與隨之而來的身體、健康和育兒負擔。
2.性政治的政治犯為數眾多
被賣或被迫為娼者,以及遭受性暴力與婚姻暴力「刑求」的被害女性,堪稱為男權體制中的女性「性政治犯」,她們由於身處恐懼之中,是調查與研究最難到達的角落,因此,其境況如何,人數多少,都仍處於黑幕之中。
根據警方所成立的掃除雛妓「正風專案」,從1987年3月1日到1991年7月6日,共查獲三百二十件人口買賣案,並查到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十六歲以下雛妓。「勵馨基金會」的一項研究推估,被賣和被迫為娼的十八歲以下少女,於1991年12月間,全台灣共存在著二千三百六十五人至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九人之間,她們的處境往往比傳統男性政治犯更加悽慘。被迫的雛妓是一面殘酷的鏡子,映照出台灣社會性關係嚴重失衡的醜態。
至於性暴力方面,根據《警務統計》,從1984年到1993年間,全台灣報案的強姦與輪姦案件共有七千四百八十七件(強姦傷害與強姦殺人除外)。依據一般了解,實際的發生數可能在此數的六倍到十倍之間。但是,被定罪、受到法律制裁的強姦犯少之又少,根據《法務統計》,從1984年到1993年的十年間,各地方法院終結的公訴刑事案件中,因強姦與強姦殺人而被判罪的僅有一千九百八十五人。這一千九百八十五人中,有強姦前科者共三百九十六人,累犯率高達20%,而又由於受害者報案率偏低,使犯案者不易留下前科記錄,因此可知實際累犯率一定遠遠高於20%。性暴力報案率低、判罪率低、再犯率高,這說明了公權力面對性暴力的無能,甚至縱容。
婚姻暴力方面,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所作的1992年《台灣省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受訪已婚婦女受丈夫毆打至於「已無法忍受」程度者有0.2%;前項加上經常被毆者有1.4%;前兩項加偶爾被毆者,則共有17.8%。根據這些數據加以估計,台灣地區已婚婦女經常受丈夫毆打的,約有七萬人,其中已經到無法忍受程度的,約有一萬人。以上數字據信應是低於實際發生數,因為受虐的婦女,尤其是情況較為嚴重者,是民調最不容易到達的死角。
以上數據顯示,有為數不少的婦女處於基本人權受嚴重侵犯的處境,而公權力卻袖手不管。
3.女性單方承受沉重的家務與照顧責任
婦女不管有無職業,都片面承擔著絕大部分家務與照顧責任,她的生涯周期大致如下:自幼與母親分擔家務——婚後(與夫之母一起)負擔夫家的家務—生育並照顧兒女一照顧年老的夫之父母—照顧孫子女一照顧老病的丈夫——面對自己的老病。不僅於此,家中的傷患和殘障者也由婦女照顧。將幼弱、老病、殘疾的沉重照顧責任丟給女人的隱形制度,使「婦女」成為我國的「福利制度」的同義詞,也使婦女受拖累,跟受她們照顧的老弱一起成為社會的弱勢。
內外兼顧更使職業婦女承受不人道的工作量。根據1990年「國民時間運用調查」,已婚職業婦女全年平均每週花在工作與家務育兒的時間,高達六十五小時(已婚有職男性則僅有五十小時),平均每週超過《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最高工時(包含法定最長加班時間),達十小時之多!這不僅顯示已婚職業婦女的超時工作,也充分暴露她們沒有休假的不人道處境。(男性的每週五十小時則在法定工時之內,足見男性中心體制的法律,一面明擺著「保護婦女」之名,限制女性的工時,一面卻遂行著「剝削女人」之實!)
4.女性工作權受剝奪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的工作權應予保障」,但台灣近年婦女勞動參與率保持低於45%,充分暴露女性工作權受到剝奪的事實。
妨礙女性工作權的原因主要有三:(一)受限於沉重的家務與照顧重擔,十五至六十四歲有工作能力卻因「料理家務」而未參與勞動的婦女,為數達二百六十萬之多!(二)許多公家和民營機構在雇用條件上歧視女性。譬如,於1995年9月舉行的外交領事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特考,總共預定錄取五十五人,其中女性名額只有八人,男性名額是女性名額的六倍!現有公務員中,經由沒有性別限制之高、普考管道而任用者,女性是男性的1.25倍(男性二萬二千人,女性二萬八千人),至於通過嚴重歧視女性的特考而任用的公務員,男性則是女性的4.3倍(男性達十一萬五千人,女性僅二萬七千人)!由於特考是政府最大量的用人管道,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特考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在於限定女性、保障男性。政府機構用人尚且如此,無怪乎勞委會對提升女性參與勞動率與消除民間雇用之性別歧視,絲毫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三)除了雇用之外,女性在升遷、進修及薪資上也備受歧視,以致大大減低其在職場上求發展的意願。
5.女性財產權受侵奪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的財產權應予保障」,但事實上女性的財產權卻備受剝奪。婦女被強制從事無酬勞家務勞役,往往因此而失去發展事業、賺取收入的機會,即連已參與勞動的婦女,也因為發展受限,薪資所得僅及男性的67%;已婚婦女的財產管理權受到法條不合理、不平等的限制,甚至連薪資和所繼承的遺產也規定由夫管理、使用和收益!此外,女性的財產繼承權普受嚴重剋扣,根據1989年「台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有80%(婆家)至83%(娘家)的家庭分家時僅兄弟分,另外,分別有8%為兄弟分得比姊妹多。
6.敎育環境歧視女性
教育環境中充斥著歧視女性的訊息和情境。教科書內容、課程安排、敎師態度、男女學生之互動、招生之性別限制,以及教育主管與家長會主導者的性別分配等方面,都有改進的必要。
尤其必須指出的是,從高中到大學二年級為期五年每週兩小時必修的「軍訓護理課程」,由軍方人士組成之「教育部軍訓處」主導課程安排,硬性規定男生學習有關領導統御和攻擊防禦的知識與技術,女生則學習跟照顧和家庭有關的知識與技術,傳遞最為僵固的傳統刻板性別角色。這是台灣過去「軍政」、「復國」時期的遺毒。
另外,父母對兒子、女兒的教育投資並不相等。1993學年度公立幼稚園學生男生女生的1.025倍,明顯低於該年齡層的人口性别比率,私立幼稚園男生是女生的1.118倍,明顯高於該年齡層的人口性別率,可見父母願意花比較多的錢讓兒子上私立幼稚園,女兒則較常被送往便宜的公立幼稚園。私立國小和國中的情況也一樣,尤其是私立國中,男生高達女生的1.368倍。
父母、學校、社會交相影響之下,女學生隨著年齡增長,逐漸在激烈的教育淘汰戰中落敗。大學日間部學生,男生是女生的1.42倍,碩士班達2.58倍,博士班更是高達5.26倍!
以上數據顯示,男性享受較多的教育的資源,高等教育的資源更是主要由男性享用。
7.決策權為男性所把持
前述種種因素使女人不易出頭,以致在決策階層中所佔的比率,遠遠低於人口中的性別比率。目前(1995年9月),我國僅有一位女性閣員(衛生署署長);另外,十職等以上的公務員中,女性僅佔7.7%。各級民意代表的部分,立法委員中女性佔10.6%(十七名),國民大會代表中
佔14%(五十七名),省議會中女性議員佔20.3%(十六名),台北市議員中佔23.1%(十二名),高雄市議員中佔13.6%(六名);各縣市議員中女性平均佔15.2%(共一百二十八名),鄉鎮及縣轄市民代表中佔15%(五百八十七名)。民選行政首長的部分,省及院轄市長中沒有女性;縣
及省轄市長中僅有一名女性(嘉義市長);鄉鎮及縣轄市長中,僅有六名女性(佔1.94%)。
8.國家生育政策和傳宗接代律法掌控女人身體
我國的法律、習俗和政策,對女性的性和生育行為實施控制。有關人口與生育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優生保健法》、《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和所謂的「家庭計畫」政策,隱含著一個明確的雙重目的:保護父權家庭,並調節國家需要(包括國家經濟負擔、生產力需求、人口結構等等考量)。由於決策者為男性,而且訴求的對象為父權社會,生育政策在推行少生時叫女人單方承擔避孕的責任,而在推行多生時則從未將托育重擔納入考慮。
生育政策一方面否定女人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大幅度依賴醫療專業,導致女性身體醫療化的負作用,令女人盲目相信醫療,以致產生眾多「沒有子宮的女人」、「沒有甲狀腺的女人」等怪異現象。
此外,現有習俗與法律都執迷於「子傳父姓」的宗法,以致已婚女性仍然普遍承受「生子」壓力。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所作1992年《台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高達84.6%的受訪女性認為應該要有兒子,認為應該有兩個以上兒子的也有55.8%,甚至連年輕高學歷者亦不例外,認為應該有兩個以上兒子的,二十至二十九歲婦女有39.1%,大專以上學歷婦女也仍高達35.3%。
在生子的壓力下,婦女紛紛求助偏方與醫學。1947年至1956年的十年間,台灣地區平均出生男女比例為105.6比100,符合世界各民族普遍的自然比例,但是,此後隨著生育科技運用的普及,差距便越拉越大。尤其是絨毛檢查術於1987年前後開始為私人診所廣泛應用之後,出生嬰兒性別比例於1987年首度突破108。從1990年至1992的三年間,出生男女嬰性別比例更是平均高達110.22。其後,顯係由於絨毛檢查術所導致的嬰兒畸形廣受報導,1993年出生嬰兒性別比例驟然降為108.58;這由於絨毛檢查術有否使用而導致的一點六個百分點(大約等於二千五百名女嬰)之明顯差距,無疑是個鐵證,告訴我們:「墮女嬰」的事實普遍存在於台灣。若拿1947年至1956年之間的105.6的比例作基準,則1990年至1992年的三年間,每年平均大約「蒸發」或「少生」七千一百多名女嬰;1993年雖然稍緩,但被蒸發的女嬰也大約有四千六百多名。
每年消失無蹤的數千名女嬰,正和被迫為娼的婦女,以及眾多性暴力與婚姻暴力的重度受害者一樣,指明恐怖統治的存在。此類現象令女人思之不寒而慄。試問,連生存權和人身自由都可以因性別因素而受剝奪,女人又還有哪項權利是不可被剝奪的?無怪乎《憲法》所規定應受保障的各項人民權利,法律與習俗莫不將之一一從女人身上奪走。
9.老年女人處境堪憂
在幾乎所有權利都受剋扣或剝奪之後,犧牲奉獻了一輩子的老年女人發現,她面對的是一個孤單且毫無保障的晚年。根據<民法繼承編>規定,未亡人(通常是女人)與子女共同平均繼承。這使得素來依賴丈夫、沒有個人財產的老年女人,往往因失去丈夫與丈夫的大部分財產而淪於貧困,而且,在實務上她經常無法從丈夫那兒繼承到不動產的所有權,以致落入寄人籬下的苦境。新近實施的《健康保險法》對慢性病的長期看護並未提供任何支助,這不僅意味長期看護仍被視為女人的責任,更意味女人自己所需的看護絲毫不受保障。而執政黨刻正籌畫的國民年金制度,將根據職業決定年金的有無,如此,因負家務與照顧之責而不克就業的眾多婦女,將於老年承受二度剝奪。
總之,在我們的國和家中,女人的幾乎所有權利,都隨時可能受到非法或甚至合法的侵奪。這些權利到哪裡去了呢?女性主義理論家們不時提醒習慣於——太習慣於——犧牲奉獻的女人,要常常自問並互問:誰得到利益?
誰得到利益?答案很明顯:男人全體。例如:為人妻者必須侍奉公婆,她們的兄弟於是說她們沒有奉養父母,所以不應繼承財產,就把財產給霸佔,並且叫他們的妻子侍奉公婆;如此,女人的丈夫和兄弟利害與共。就連一般人所深惡痛絕的性暴力,也呈現性暴力犯和好男人共犯的狀況:好男人必須依靠性暴力罪行對(所有)女人所造成的恫嚇,才有正當理由對女人的性與身體實施禁錮(這是父權血統之所依賴),性暴力於是隱然受到系統性的保護,成為一切種類的犯罪當中報案率最低者。接下去,男性主政者和主管們便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女人因為有遭受性暴力的危險,並且必須費心費力侍奉家人,沒有多餘的心力,所以不適合這個職務那個職務。如此,整體男人和個別男人得以霸佔權力與利益。
二、男女共治共享的國家藍圖
從以上的描述可知,我國《憲法》第一條所說的「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實際意涵應是「中華男國為男有男治男享之男主不和國」。這無疑是很令人難堪的騙局,在被揭穿之後,相信無論女人或男人都會願意盡力去改正它。
我們要知道,「男有男治男享」的排他性、壓榨性體制,必然造成一個男人專事爭奪歛聚的社會。要想改正它,基本的方向無疑是:創造一個人人共治共享的新國家,建立以所有人的需要為基本考量的新制度和新政策。這巨大的變動,在歷史的此刻,關鍵無疑在於「男女共治」與「以女性觀點為中心考量」。階段性的「以擔任照顧者的無聲弱勢女性之
觀點為中心考量」,據信將能發揮矯枉的功效,導引社會邁向全民共治共享的新境界。
為了邁向全民共治共享,必須推行前述以女性觀點為中心考量的制度與政策,其必要條件與措施有三:調整國家目標與國家架構,推行男女共掌決策權,以及設置各級兩性平等委員會與執行單位。茲簡要說明如下:
1.國家目標與國家架構的調整:
從復國與官商勾結到照顧人民生活
國民黨政權自遷入台灣至1987年「戒嚴令」取消的四十餘年間,方面(至少在名義上)將國家目標界定為「反共(攻)復國」,舉著「國家至上」的大羈,把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當作實現這項偉大目標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實質上)進行著層面廣泛的官商緊密聯結。這樣的政策走向,對女性造成很大的影響。「反攻復國」時期所肇始的軍訓教育,強制教育女性扮演照顧者的角色(這是來自於「男人當兵、女人當護士」的軍方邏輯);偏重軍事的施政將大量預算放在國防上,與女性息息相關的生活面向受到排擠和忽視,女人必須用個人微小的力量獨自承擔對小孩、老人和殘障者的照顧。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二分之下,官商的勾結成為男性官員與男性商人的勾結,以致權力與利益為男性權貴所把持,女人與尋常百姓的需求益加受忽視。尤其必須指出的是,男性觀點的國土政策,使空間的使用嚴重歧視女性、小孩和老人。譬如,男人佔用大片大片的高爾夫球場,他們一人一部的汽車、機車塞滿了道路、污染了空氣,而留給女人、小孩和老人的,卻是簡陋、狹隘、嘈雜、炎熱、空氣污濁的幼稚園、學校與公園。對於這一切,不負責照顧小孩和老人的男人,尤其是權貴男人,是不可能認真地去尋求解決的。
今天要革新台灣社會,使一般人能夠享受安全舒適的生活,我們所剩的可以信賴的觀點,無疑是女性的觀點,而且我們所剩的立即可用的力量,無疑也是女人的力量。這乃是因為在歷史的此刻,民生面向的知識和技術為女人所獨有。這眞正是一個烹小鮮者最適合治國的時代,我們有必要宣導觀念、制定政策,制度性地將治國之權付託給女人。
基於以上的觀點,我們的國家架構與施政方向應立即作如下的調整,以使女性觀點下的要事(也就是傳統男性觀點下的「小事」、「女人家的事」)能夠成為國家施政的重心。
(一)國家預算應予大幅調整。應大幅減少軍事預算,包括隱藏在教育預算(如軍訓教育和軍校教育的預算)、福利預算(如退輔預算)等等中的軍事費用,而將經費用在托育、幼教、安養、大眾運輸、環境保護、大衆休閒等面向,以便充分照顧人民的生活。俟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社會內部所鬱積的壓力與憤恚得以消減之時,治安預算也將可以大幅削減。
(二)國土應重新規畫,以便托兒所、學校、安養院、大眾運輸系統、大眾休閒場所等設施能優先得到充裕的空間。
(三)應盡速建立社工與福利體系。國民身心的照顧必須依賴完善的社福支持網路,但是,以往國防與經貿掛帥的國家架構,始終於設置社福體系,以致今天所有這方面的需求,即使是已經明文立法保障的(如對受虐兒童的保護),也完全無法落實。
(四)應將現行兵役法改為社會服務役,並廢除徵兵制,實施募兵制。全面性的福利制度實施之後,社會服務的需求將大量增加,應以社會服務役因應此需求。社會服務役應在政府專責機構(如社工、環保等機構)的主導之下從事服務,可以作為年輕人步入社會之前的成年禮或準備階段。現有的兵役有兩個很大的缺點:(1)它只徵召男性,造成兩性之間的隔離與不平;(2)它對年輕男性實施著甚為負面的「成年禮」,其不良影響包括養成敷衍和形式化的態度、培養剛猛的心性與使用暴力的技巧,以及在氣氛剛暴的男性團體中學習視女人為異類、次等人、性的發洩對象。若以社會服務役取代之,可以預期將不僅能節省國家預算,符合社會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男女平等合作、深入社會與人民互動的性質,無疑將使它成為深具正面意義的成年禮,能夠在每一個年輕人步入社會之前,提供他(她)充分的機會,用以學習熟悉社會、關照他人。
總之,我們應該從女性的觀點進行國家目標和國家架構的重新調整,這樣相信能為苦於暴力與金權的今日台灣帶來新生的機會。
2.立即全面推行男女共掌決策權
我們已可確知,許多現存的父權體系在遠古時代都有母權的前身。這些母權前身都被遺忘了,被貶為「史前」、「非信史」,彷彿現有的文明不是她的子裔,他必須明確否認跟她的關聯。這種態度是充分的證據,顯示遠古女性的權力會被強制奪走,以及遠古母權的史蹟會被強制抹除。今天,在性別關係再度進入轉型期之際,遠古的母權激發我們思考:女人無疑有權奪回權力,但是,那是什麼樣的權力呢?那會不會也是一個單一性別——女性——擅權的時代?我們要不要回到那種時代呢?這種思考足以令我們確信應該確立兩個原則:一為「男女平權」,另一為「把女人該有的權力還給女人」。這兩個原則應用在決策權的性別分配重整,應從底下三個方向同時進行。
第一個方向是:「把權力交給負實際責任的女人」。在父權體制中,女人負擔著沉重的責任,但卻被迫聽命於父權的規條,而不被賦予自主作決策的權力。有責者無權,造成決策不符合實際需要,以及女人的無奈、無力甚至低能化。因此,我們應該立即還權於女人,包括:教育當局主管、各級學校校長和主任的性別比率應與教師的性別比率相當,中小學之家長會,應由一般實際照顧小孩生活與功課的母親們主導,社區事務主導者(村里鄰長、各區或鄉鎮協調會委員等)應優先由嫻熟私領域事務的性別(即女性)擔任等等。
第二個方向是:「把權力交給有能力的女人」。女人是弱勢,而絕非弱者或能力低落者。女人往往具有高強的能力,但她應有的職位與發揮能力的機會,卻經常因性別或性別角色的因素而受剝奪。譬如,國家特種考試施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厲行公務員任用之限制女性、優待男性政策。如此必然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譬如,1992年外交與國際新聞、金融人員特考,預定錄取名額男性是女性的七倍,結果有些項目筆試最低錄取分數男性比女性低了十幾分之多!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高中和大學學生輔導人員的任用。教育部軍訓處限定由以男性居多的軍訓教官擔任學生輔導工作,霸佔了以女性居多的心理、社工、教育、輔導等科系畢業生的適任職位。我們相信,類似這種作法不僅使國家錯失有能力的女性,而且也養成了男性特權、擅權與濫權的心態,以致整個社會蒙受其害。「機會均等」原則的運用無疑也應涵蓋女人,以便所有有能力的女人都能得到她應有的職位。
第三個方向為:「決策應融合兩性觀點」。社會與人生的所有面向都需要兩性觀點,缺少了哪個性別的觀點,那個性別便將因此吃虧,社會也會因此失衡。掌權的男性懂得其中奧妙,因此規定保障護士、小學教師等傳統女性職業的男性名額。但是,社會上卻有太多面向缺乏女性觀點,譬如:治安、國防、工會......等等。挪威法律規定,任何官方或人民團體的決策團(理事會、委員會等等),凡是人數達四人或四人以上的,其較少的性別至少應有兩人,而且「應盡可能達到兩性代表權的平等」。這應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總之,我們應該形成重用女人的社會共識,並透過共識而形成壓力,促使政黨與官方、民間機構和團體用心栽培並擢用女性。
3.兩性平等專責機構的設置
台灣婦運的興起,最主要的因素無疑是時代的需要;台灣無疑已進入兩性關係與性別觀點急須調整的階段。但是,兩性平等所牽涉的範圍甚廣,層面極深,如果毫無章法地去做,一定會弄得一團糟,因此,有必要設置專責機構。
我們不妨參考聯合國的規定,與瑞典、挪威等國的設計,而設置底下兩套互相輔成的體系:(一)兩性平等委員會,是設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中的獨立機構,統籌負責對所有兩性平等事宜進行觀測、研究與決策;(二)兩性平等司(局、處、室等),普遍設於各級政府相關機構內部,是前項決策機構的執行單位。這種設計可以確保決策的確切、可行與有效。
4.全民福利國與兩性關係的調整
以上所描述的男女共治共享、兼融兩性觀點的福利國,是一個全面性、全民性的福利國,而不是現行的父權資本主義體系底下的救助性、附屬性補救機構。
現行的父權資本主義體系,也就是「男有男治男享」的體制,所實施的福利制度,是一個救助性的制度。這種父權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色在於:(一)國家與權貴男性和所有父、夫形成緊密聯結,這些人和其餘成員之間則形成主從關係;國家和這些從屬性成員——尤其是女人——之間並無直接關聯,它也不以照顧他們為職責。(二)國家讓權貴男性聯合所有為父、夫者,瓜分並霸佔所有資產與資源,因此,這些男性雖然一方面互相聯結,另一方面卻進行著激烈的斂聚與爭奪;國家並以協助這斂聚與爭奪的活動為己任,因而必然致力於國與國之間的爭奪,以及以爭奪和自保為目的的聯結,國家資源於是被大量投注於所謂「國防」和「外
交」。(三)當依附者(即女人和輩分、位階卑下的男人)因失去依附而跌落體系邊緣時,國家就拋給他們所謂「福利」的微小救生圈,從此任他們在生存的警戒線上載浮載沉。
我們想要提出來的替代方案,是全面性、全民性的福利國家。這樣的國家以協助人民過好的生活為主要職責,它的國際關係亦以此為目標;它視自己為達到前述目標的施政單位,其他的名堂(如民族主義等)都是次要的;它推行人人共治、共享的參與式民主制度(participatory democracy),自立、參與、互助是其人民的基本公德,連福利的重度依賴者(如衰老、殘障者)亦不例外;它由於實施高度所得重新分配制,以及全面性的國民生活照顧,因此福利的所有提供者也同時是福利的受惠者,施與受在制度上的平衡,會在大部分國民個人的手與口袋之間達成。
在全民福利國裡,性別角色有兩個特色:一為它的延續性。傳統女人的工作在大量移至公領域,受到充分保障,大幅度破除女人對男人的從屬之後,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仍然主要是女人的工作。這性別角色的延續性使得這套制度成為有以想像、可被接受,能夠實現的。
二為它的可變性與彈性。在全民福利國中,傳統女人的工作質變為受國家預算全力支持的重要工作,這也就是福利體系裡的工作,如此,女人成為這個國家的重要體系的從事者與主導者。在福利體系為女人爭得工作與權力之後,整體女人力量的增加,又將能進一步推出眞正代表女性觀點的(女性)國家主導者。如此,將可徹底打破男尊女卑的舊性別關係,從此展開男女平等、性別角色多元化的嶄新時代。